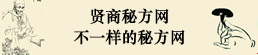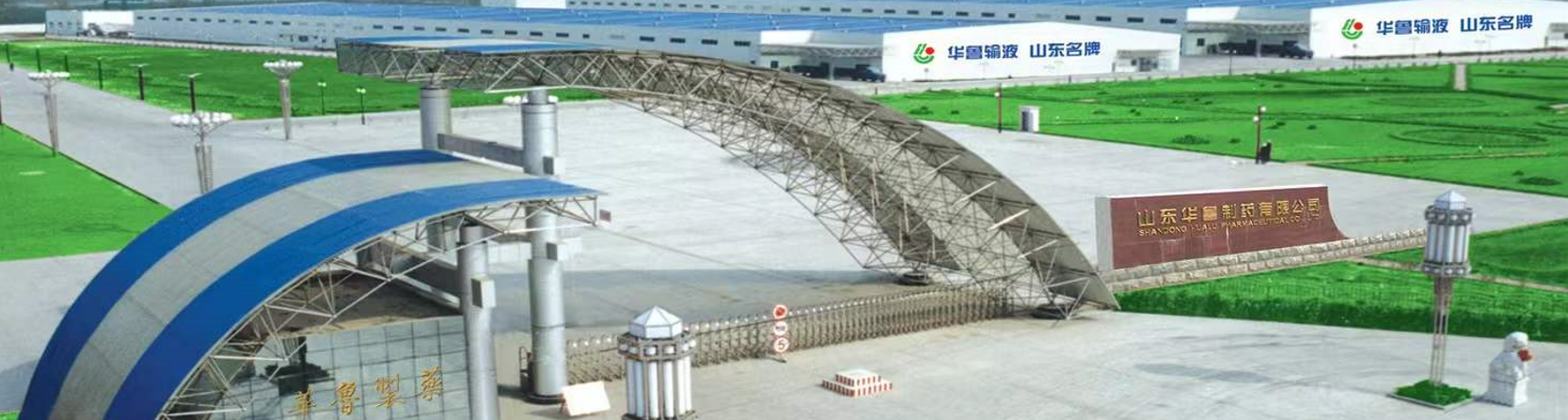皇甫谧-古代名中医

魏晋间作家、医学家。
提起皇甫谧,人们可能立刻想到他编撰的《针灸甲乙经》。其实,除此之外,他还编撰了《帝王世纪》、《高士传》、《逸士传》、《列女传》、《元晏先生集》等书。他一生以著述为业。在医学史和文学史上都负有盛名,尤其 在医学上,是我国中医领域“针灸疗法”的创始人。
皇甫谧,幼名静,字士安,自号玄晏先生,是东汉太尉皇甫嵩的曾孙,拜乡人席坦为师。安定朝那(今甘肃灵台县朝那镇)人。生于东汉建安二十年(公元二一五年),卒于西晋太康三年(公元二八二年),活了六十八岁。
也有考证为:皇甫谧出生东汉朝那(音zhu nuo),今宁夏彭阳县。彭阳县在东汉时期为朝那城,城址为今彭阳县城西二十公里处古城镇。迄今还存在当时朝那城遗址,当时镇守朝那城的为东汉一王侯,其墓室也被发现,但已被严重破坏。
皇甫谧小时候,过继给叔父,迁居新安(今河南渑池县)。叔父、叔母,尤其是叔母,很疼爱他。而皇甫谧自幼贪玩,无心向学,人们笑他是傻子。到了十七岁,人高马大,竟“未通书史”,整天东游西荡,象脱缰的马,叔母对皇甫谧如此调皮捣蛋非常气愤,恨铁不成钢,常常为他的前途而忧虑。一天,她把贪玩的皇甫谧赶出家门,想要教训他。谁知他到了外边弄来了香瓜、甜果之类,洋洋自得地呈献给叔母,以为如此“孝顺”一番,便可平息叔母的盛怒。谁知叔母更加气愤,接过瓜果,狠狠地摔在地上,流着泪说:“你快二十岁了,还是‘志不存教,心不入道’,你要真心孝顺父母,就得‘修身笃学’”。他很受感动,噙着泪花发誓要悔过自新,改弦更张,矢志苦学。从此以后,他刻苦攻读,虚心求教,一天也不懈怠。下定决心要编著一部针灸学专书。
对于针灸方面的经验,早在二千多年前,我国医家已进行了系统总结。如一九七三年在湖南长沙和马三堆汉墓中,发现了多种周代编写的医书,其中有《足臂十一脉灸经》和《阴阳十一脉灸经》。战国时代的《黄帝内经》也有许多论述针灸的内容。东汉初期针灸名医涪翁还有《针经》的专述。但是晋代以前涉及到针灸内容的医书,“其父深奥”,“文多重复,错互非一”。加上当时用竹木简刻书,书被视为秘宝,普通的人是不易得到的。由于参考书奇缺,这给皇甫谧编撰工作带来很大困难。然而值得庆幸的是,皇甫谧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。他用百折不挠的精神,设法借来了需要的医书,经穷搜博采,获得了大量的资料。他把古代著名的三部医学著作,即《素问》,《针经》(即《灵枢》),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,纂集起来,加以综合比较,“删其浮辞,除其重复,论其精要”,,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验,终于写出了一部为后世针灸学树立了规范的巨著—《黄帝 三部针灸甲乙经》,也称《针灸甲乙经》,简称《甲乙经》。
《针灸甲乙经》,共十卷,一百二十八篇。内容包括脏腑、经络、腧穴、病机、诊断、治疗等。书中校正了当时的腧穴总数的穴位654个(包括单穴48个),记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和禁忌,说明了各种操作方法。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联系实际,有重大价值的针灸学专著,被人们称做“中医针灸学之祖”,一向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之一。唐代医家王焘评它“是医人之秘宝,后之学者,宜遵用之”。此书问世后,唐代医署就开始设立针灸科,并把它作为医生必修的教材。晋以后的许多针灸学专著,大都是在参考此书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而写出来的,也都没有超出它的范围。直至现在,我国的针灸疗法,虽然在穴名上略有变动,而在原则上均本于它。一千六百多年来,它为针灸医生提供了临床治疗的具体指导和理论根据。
此书也传到国外,受到各国,特别是日本和朝鲜的重视。公元七O一年,在日本法令《大宝律令》中明确规定用《针灸甲乙经》列为必读的参考书之一。足见,皇甫谧的《针灸甲乙经》影响之深远。
他抱病期间,自读了大量的医书,尤其对针灸学十分有兴趣。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,他发现以前的针灸书籍深奥难懂而又错误百出,十分不便于学习和阅读。于是他通过自身的体会,摸清了人身的脉络与穴位,并结合《灵枢》、《素问》和《名堂孔穴针灸治要》等书,悉心钻研,著述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的著作——《针灸甲乙经》。
该书除了论述有关脏腑、经络等理论,还记载了全身穴位649个,穴名349个,并对各穴位明确定位,对各穴的主治证、针灸操作方法和禁忌等都做了详细描述,并一一纠正了以前的谬误。
可以说,《针灸甲乙经》是针灸学发展中的一部重要著作,唐朝太医署在学习针灸学时就是以该书为教材的。后来,此书流传到了日本、朝鲜等国家,在国际上声望也很高。
40岁时,他患了风痹病,十分痛苦,在学习上却仍是不敢怠慢。有人不解他为何对学习如此沉迷,他说:“朝闻道,夕死可也。”说如果早上明白了一个道理,就算晚上便死去,也是值得的。皇帝敬他品格高尚、学识丰富,便请他做官,他不但回绝了,竟然还向皇上借了一车的书来读,也算得上是一桩奇事了!
其《帝王世纪》为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,记录了各代帝王时期的地亩、属国、人口。他对先秦时代的人口估计是目前人口历史研究中的重要资料,一直为历代学者所引用,但近代一些学者也对此持怀疑态度。
晚年,皇甫谧曾多次被征召为孝廉,他“连辟公府不就”,就连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他也委婉拒绝了,并向武帝借了一车书供学习。最后于太康三年以布衣生份而卒。——《晋书,皇甫谧传》
晋书 卷五十一
皇甫谧,字士安,幼名静,安定朝那人,汉太尉嵩之曾孙也。出后叔父,徙居新安。年二十,不好学,游荡无度,或以为痴。尝得瓜果,辄进所后叔母任氏。任氏曰:「《孝经》云:'三牲之养,犹为不孝。'汝今年余二十,目不存教,心不入道,无以慰我。」因叹曰:「昔孟母三徙以成仁,曾父烹豕以存教,岂我居不卜邻,教有所阙,何尔鲁钝之甚也!修身笃学,自汝得之,于我何有!」因对之流涕。谧乃感激,就乡人席坦受书,勤力不怠。居贫,躬自稼穑,带经而农,遂博综典籍百家之言。沈静寡欲,始有高尚之志,以著述为务,自号玄晏先生。著《礼乐》、《圣真》之论。后得风痹疾,犹手不辍卷。
或劝谧修名广交,谧以为「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,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、舜之道,何必崇接世利,事官鞅掌,然后为名乎」。作《玄守论》以答之,曰:
或谓谧曰:「富贵人之所欲,贫贱人之所恶,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?且道之所贵者,理世也;人之所美者,及时也。先生年迈齿变,饥寒不赡,转死沟壑,其谁知乎?」
谧曰:「人之所至惜者,命也;道之所必全者,形也;性形所不可犯者,疾病也。若扰全道以损性命,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?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,形强犹不堪,况吾之弱疾乎!且贫者士之常,贱者道之实,处常得实,没齿不忧,孰与富贵扰神耗精者乎!又生为人所不知,死为人所不惜,至矣!喑聋之徒,天下之有道者也。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,以为损也;一人生而四海笑者,以为益也。然则号笑非益死损生也。是以至道不损,至德不益。何哉?体足也。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之祸,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,岂道德之至乎!夫唯无损,则至坚矣;夫唯无益,则至厚矣。坚故终不损,厚故终不薄。苟能体坚厚之实,居不薄之真,立乎损益之外,游乎形骸之表,则我道全矣。」
遂不仕。耽玩典籍,忘寝与食,时人谓之「书淫」。或有箴其过笃,将损耗精神。谧曰:「朝闻道,夕死可矣,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!」
叔父有子既冠,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,遂还本宗。
城阳太守梁柳,谧从姑子也,当之官,人劝谧饯之。谧曰:「柳为布衣时过吾,吾送迎不出门,食不过盐菜,贫者不以酒肉为礼。今作郡而送之,是贵城阳太守而贱梁柳,岂中古人之道,是非吾心所安也。」
时魏郡召上计掾,举孝廉;景元初,相国辟,皆不行。其后乡亲劝令应命,谧为《释劝论》以通志焉。其辞曰:
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,及泰始登禅,同命之士莫不毕至,皆拜骑都尉,或赐爵关内侯,进奉朝请,礼如侍臣。唯余疾困,不及国宠。宗人父兄及我僚类,咸以为天下大庆,万姓赖之,虽未成礼,不宜安寝,纵其疾笃,犹当致身。余唯古今明王之制,事无巨细,断之以情,实力不堪,岂慢也哉!乃伏枕而叹曰:「夫进者,身之荣也;退者,命之实也。设余不疾,执高箕山,尚当容之,况余实笃!故尧、舜之世,士或收迹林泽,或过门不敢入。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,遇时也。故朝贵致功之臣,野美全志之士。彼独何人哉!今圣帝龙兴,配名前哲,仁道不远,斯亦然乎!客或以常言见逼,或以逆世为虑。余谓上有宽明之主,下必有听意之人,天网恢恢,至否一也,何尤于出处哉!」遂究宾主之论,以解难者,名曰《释劝》。
客曰:「盖闻天以悬象致明,地以含通吐灵。故黄钟次序,律吕分形。是以春华发萼,夏繁其实,秋风逐暑,冬冰乃结。人道以之,应机乃发。三材连利,明若符契。故士或同升于唐朝,或先觉于有莘,或通梦以感主,或释钓于渭滨,或叩角以干齐,或解褐以相秦,或冒谤以安郑,或乘驷以救屯,或班荆以求友,或借术于黄神。故能电飞景拔,超次迈伦,腾高声以奋远,抗宇宙之清音。由此观之,进德贵乎及时,何故屈此而不伸?今子以英茂之才,游精于六艺之府,散意于众妙之门者有年矣。既遭皇禅之朝,又投禄利之际,委圣明之主,偶知己之会,时清道真,可以冲迈,此真吾生濯发云汉、鸿渐之秋也。韬光逐薮,含章未曜,龙潜九泉,坚焉执高,弃通道之远由,守介人之局操,无乃乖于道之趣乎?
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,五教班叙则人理定。如今王命切至,委虑有司,上招迕主之累,下致骇众之疑。达者贵同,何必独异?群贤可从,何必守意?方今同命并臻,饥不待餐,振藻皇涂,咸秩天官。子独栖迟衡门,放形世表,逊遁丘园,不睨华好,惠不加人,行不合道,身婴大疢,性命难保。若其羲和促辔,大火西穨,临川恨晚,将复何阶!夫贵阴贱璧,圣所约也;颠倒衣裳,明所箴也。子其鉴先哲之洪范,副圣朝之虚心,冲灵翼于云路,浴天池以濯鳞,排阊阖,步玉岑,登紫闼,侍北辰,翻然景曜,杂沓英尘。辅唐、虞之主,化尧舜、之人,宣刑错之政,配殷、周之臣,铭功景钟,参叙彝伦,存则鼎食,亡为贵臣,不亦茂哉!而忽金白之辉曜,忘青紫之班瞵,辞容服之光粲,抱弊褐之终年,无乃勤乎!」
主人笑而应之曰:「吁!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,未睹幽人之仿佛也;见俗人之不容,未喻圣皇之兼爱也;循方圆于规矩,未知大形之无外也。故曰,天玄而清,地静而宁,含罗万类,旁薄群生,寄身圣世,托道之灵。若夫春以阳散,冬以阴凝,泰液含光,元气混蒸,众品仰化,诞制殊征。故进者享天禄,处者安丘陵。是以寒暑相推,四宿代中,阴阳不治,运化无穷,自然分定,两克厥中。二物俱灵,是谓大同;彼此无怨,是谓至通。
若乃衰周之末,贵诈贱诚,牵于权力,以利要荣。故苏子出而六主合,张仪入而横势成,廉颇存而赵重,乐毅去而燕轻,公叔没而魏败,孙膑刖而齐宁,蠡种亲而越霸,屈子疏而楚倾。是以君无常籍,臣无定名,损义放诚,一虚一盈。故冯以弹剑感主,女有反赐之说,项奋拔山之力,蒯陈鼎足之势,东郭劫于田荣,颜阖耻于见逼。斯皆弃礼丧真,苟荣朝夕之急者也,岂道化之本与!
若乃圣帝之创化也,参德乎三皇,齐风乎虞、夏,欲温温而和畅,不欲察察而明切也;欲混混若玄流,不欲荡荡而名发也;欲索索而条解,不欲契契而绳结也;欲芒芒而无垠际,不欲区区而分别也;欲暗然而内章,不欲示白若冰雪也;欲醇醇而任德,不欲琐琐而执法也。是以见机者以动成,好遁者无所迫。故曰,一明一昧,得道之概;一弛一张,合礼之方;一浮一沈,兼得其真。故上有劳谦之爱,下有不名之臣;朝有聘贤之礼,野有遁窜之人。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,李老寄迹于西邻,颜氏安陋以成名,原思娱道于至贫,荣期以三乐感尼父,黔娄定谥于布衾,干木偃息以存魏,荆、莱志迈于江岑,君平因蓍以道著,四皓潜德于洛滨,郑真躬耕以致誉,幼安发令乎今人。皆持难夺之节,执不回之意,遭拔俗之主,全彼人之志。故有独定之计者,不借谋于众人;守不动之安者,不假虑于群宾。故能弃外亲之华,通内道之真,去显显之明路,入昧昧之埃尘,宛转万情之形表,排托虚寂以寄身,居无事之宅,交释利之人。轻若鸿毛,重若泥沈,损之不得,测之愈深。真吾徒之师表,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。子议吾失宿而骇众,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。
夫才不周用,众所斥也;寝疾弥年,朝所弃也。是以胥克之废,丘明列焉;伯牛有疾,孔子斯叹。若黄帝创制于九经,岐伯剖腹以蠲肠,扁鹊造虢而尸起,文挚徇命于齐王,医和显术于秦、晋,仓公发秘于汉皇,华佗存精于独识,仲景垂妙于定方。徒恨生不逢乎若人,故乞命诉乎明王。求绝编于天录,亮我躬之辛苦,冀微诚之降霜,故俟罪而穷处。
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,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:「臣以尪弊,迷于道趣,因疾抽簪,散发林阜,人纲不闲,鸟兽为群。陛下披榛采兰,并收蒿艾。是以皋陶振褐,不仁者远。臣惟顽蒙,备食晋粟,犹识唐人击壤之乐,宜赴京城,称寿阙外。而小人无良,致灾速祸,久婴笃疾,躯半不仁,右脚偏小,十有九载。又服寒食药,违错节度,辛苦荼毒,于今七年。隆冬裸袒食冰,当暑烦闷,加以咳逆,或若温虐,或类伤寒,浮气流肿,四肢酸重。于今困劣,救命呼噏,父兄见出,妻息长诀。仰迫天威,扶舆就道,所苦加焉,不任进路,委身待罪,伏枕叹息。臣闻《韶》《卫》不并奏,《雅》《郑》不兼御,故郤子入周,祸延王叔;虞丘称贤,樊姬掩口。君子小人,礼不同器,况臣糠<麦黄>,糅之雕胡?庸夫锦衣,不称其服也。窃闻同命之士,咸以毕到,唯臣疾疢,抱衅床蓐,虽贪明时,惧毙命路隅。设臣不疾,已遭尧、舜之世,执志箕山,犹当容之。臣闻上有明圣之主,下有输实之臣;上有在宽之政,下有委情之人。唯陛下留神垂恕,更旌瑰俊,索隐于傅岩,收钓于渭滨,无令泥滓久浊清流。」谧辞切言至,遂见听许。
岁余,又举贤良方正,并不起。自表就帝借书,帝送一车书与之。谧虽羸疾,而披阅不怠。初服寒食散,而性与之忤,每委顿不伦,尝悲恚,叩刃欲自杀,叔母谏之而止。
济阴太守蜀人文立,表以命士有贽为烦,请绝其礼币,诏从之。谧闻而叹曰:「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,而以革历代之制,其可乎!夫'束帛戋戋',《易》之明义,玄纁之贽,自古之旧也。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,席上之珍以待聘。士于是乎三揖乃进,明致之难也;一让而退,明去之易也。若殷汤之于伊尹,文王之于太公,或身即莘野,或就载以归,唯恐礼之不重,岂吝其烦费哉!且一礼不备,贞女耻之,况命士乎!孔子曰:'赐也,尔爱其羊,我爱其礼。'弃之如何?政之失贤,于此乎在矣。」
咸宁初,又诏曰:「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,守学好古,与流俗异趣,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。」谧固辞笃疾。帝初虽不夺其志,寻复发诏征为议郎,又召补著作郎。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,并不应。著论为葬送之制,名曰《笃终》,曰:
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,人理之必至也。故礼六十而制寿,至于九十,各有等差,防终以素,岂流俗之多忌者哉!吾年虽未制寿,然婴疢弥纪,仍遭丧难,神气损劣,困顿数矣。常惧夭陨不期,虑终无素,是以略陈至怀。
夫人之所贪者,生也;所恶者,死也。虽贪,不得越期;虽恶,不可逃遁。人之死也,精歇形散,魂无不之,故气属于天;寄命终尽,穷体反真,故尸藏于地。是以神不存体,则与气升降;尸不久寄,与地合形。形神不隔,天地之性也;尸与土并,反真之理也。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,死何故隔一棺之土?然则衣衾所以秽尸,棺椁所以隔真,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;季孙玙璠比之暴骸;文公厚葬,《春秋》以为华元不臣;杨王孙亲土,《汉书》以为贤于秦始皇。如今魂必有知,则人鬼异制,黄泉之亲,死多于生,必将备其器物,用待亡者。今若以存况终,非即灵之意也。如其无知,则空夺生用,损之无益,而启奸心,是招露形之祸,增亡者之毒也。
夫葬者,藏也,藏也者,欲人之不得见也。而大为棺椁,备赠存物,无异于埋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。虽甚愚之人,必将笑之。丰财厚葬以启奸心,或剖破棺椁,或牵曳形骸,或剥臂捋金环,或扪肠求珠玉。焚如之形,不痛于是?自古及今,未有不死之人,又无不发之墓也。故张释之曰:「使其中有欲,虽固南山犹有隙;使其中无欲,虽无石椁,又何戚焉!」斯言达矣,吾之师也。夫赠终加厚,非厚死也,生者自为也。遂生意于无益,弃死者之所属,知者所不行也。《易》称「古之葬者,衣之以薪,葬之中野,不封不树」。是以死得归真,亡不损生。
故吾欲朝死夕葬,夕死朝葬,不设棺椁,不加缠敛,不修沐浴,不造新服,殡?含之物,一皆绝之。吾本欲露形入坑,以身亲土,或恐人情染俗来久,顿革理难,今故觕为之制,奢不石椁,俭不露形。气绝之后,便即时服,幅巾故衣,以遽除裹尸,麻约二头,置尸床上。择不毛之地,穿坑深十尺,长一丈五尺,广六尺,坑讫,举床就坑,去床下尸。平生之物,皆无自随,唯赍《孝经》一卷,示不忘孝道。遽除之外,便以亲土。土与地平,还其故草,使生其上,无种树木、削除,使生迹无处,自求不知。不见可欲,则奸不生心,终始无怵惕,千载不虑患。形骸与后土同体,魂爽与元气合灵,真笃爱之至也。若亡有前后,不得移祔。祔葬自周公来,非古制也。舜葬苍梧,二妃不从,以为一定,何必周礼。无问师工,无信卜筮,无拘俗言,无张神坐,无十五日朝夕上食。礼不墓祭,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,百日而止。临必昏明,不得以夜。制服常居,不得墓次。夫古不崇墓,智也。今之封树,愚也。若不从此,是戮尸地下,死而重伤。魂而有灵,则冤悲没世,长为恨鬼。王孙之子,可以为诫。死誓难违,幸无改焉!
而竟不仕。太康三年卒,时年六十八。子童灵、方回等遵其遗命。
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,又撰《帝王世纪》、《年历》、《高士》、《逸士》、《列女》等传、《玄晏春秋》,并重于世。门人挚虞、张轨、牛综、席纯,皆为晋名臣。